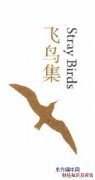感遇二首-五言古詩(shī)
admin
感遇二首
其一
蘭葉春葳蕤,桂華秋皎潔。
欣欣此生意,自爾為佳節(jié)。
誰(shuí)知林棲者,聞風(fēng)坐相悅。
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
春天的蘭草蔥郁繁茂,秋天的桂花皎明凈潔。
欣欣向榮充滿著生機(jī),各自適應(yīng)美好的季節(jié)。
誰(shuí)知道那些林中隱士,聞到了芳香深加愛(ài)悅。
花木的芬芳出于本性,何求于美人賞識(shí)攀折。
其二
江南有丹橘,經(jīng)冬猶綠林。
豈伊地氣暖,自有歲寒心。
可以薦嘉客,奈何阻重深。
運(yùn)命惟所遇,循環(huán)不可尋。
徒言樹(shù)桃李,此木豈無(wú)陰。
江南一帶生長(zhǎng)的丹橘,經(jīng)過(guò)寒冬還綠葉蔥蘢。
哪里是因?yàn)榈貧鉁嘏珣{自己有耐寒本性。
本可以獻(xiàn)給貴客嘉賓,無(wú)奈阻隔著崇山峻嶺。
命運(yùn)決定了這種遭遇,循環(huán)的道理難以追尋。
世人只是說(shuō)栽植桃李,難道丹橘就不能遮陰?
唐開(kāi)元末年,玄宗沉迷聲色,荒廢朝政,貶黜張九齡,寵信口蜜腹劍的李林甫與只會(huì)溜須拍馬的牛仙客。牛、李結(jié)成黨羽,專(zhuān)攬朝政,排除異己,致使朝政愈加腐敗。張九齡對(duì)此甚為不滿,便以比興手法,托物寓意,寫(xiě)下感情樸素真摯的《感遇十二首》。
這里的第一首即《感遇十二首》中的第一首,是一首哲理詩(shī),是詩(shī)人被貶為荊州長(zhǎng)史后所寫(xiě)。
詩(shī)一開(kāi)頭,用工整的偶句,突現(xiàn)了蘭草、桂花這兩種植物的高潔性情。由“葳蕤”二字,可見(jiàn)蘭草逢春萌發(fā)的勃勃生機(jī);由“皎潔”二字,可見(jiàn)桂花遇秋吐蕊的湛湛風(fēng)華。接下來(lái),“欣欣此生意”一句總起來(lái)說(shuō),蘭、桂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。“自爾為佳節(jié)”又分開(kāi)來(lái)說(shuō),一個(gè)“自”字,除指出蘭、桂均能應(yīng)時(shí)節(jié)而綻放外,還表明了它們雖繁盛卻不諂媚、不求人知的高尚品質(zhì),對(duì)下文的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進(jìn)行了鋪墊。
詩(shī)的前面四句只寫(xiě)蘭桂而未寫(xiě)人,第五句,詩(shī)人則用“誰(shuí)知”陡然一轉(zhuǎn),自然地引出了深居山林的美人,也就是那些蘭心桂質(zhì)的隱逸之士。美人因嗅到蘭、桂的芬芳,對(duì)蘭、桂產(chǎn)生了傾慕之情。詩(shī)由不寫(xiě)人到寫(xiě)人,是一個(gè)急轉(zhuǎn),詩(shī)情也為之一蕩。
結(jié)尾兩句,詩(shī)人又用“何求”二字將筆鋒一轉(zhuǎn)。山中美人既然愛(ài)蘭、桂的芬芳,那么,蘭、桂如有心,應(yīng)該十分愿意被美人折取賞玩。但詩(shī)人卻沒(méi)有這樣寫(xiě)下去,而是另辟新意:蘭草迎春而綻放,桂花逢秋而吐蕊,這是蘭、桂的本性,而不是為了獲得美人的攀折玩賞。可以明顯地看出,詩(shī)人以蘭、桂“不求美人折”來(lái)譬喻賢德君子的潔身自愛(ài):君子修身養(yǎng)性,只不過(guò)是他品性使然,而不是借此來(lái)獲得外界的贊譽(yù)提拔。整首詩(shī)的主旨,至此才道出。
整首詩(shī)結(jié)構(gòu)緊密、語(yǔ)盡意深,托物寓意,寓理于詠,令讀者絲毫感覺(jué)不到說(shuō)教的突兀。
《感遇十二首》中的第二首也依然是托物言志詩(shī),借歌頌丹橘表達(dá)詩(shī)人遭受排擠的憤懣心情和堅(jiān)貞不屈的節(jié)操。看到本詩(shī),人們很容易想起屈原的《橘頌》。本詩(shī)開(kāi)篇便說(shuō)“江南有丹橘,經(jīng)冬猶綠林”,其托物言志之意非常明顯。在南國(guó),深秋時(shí)多數(shù)樹(shù)木的葉片都會(huì)枯黃凋零,更別說(shuō)能經(jīng)受寒冬的摧殘。可是,丹橘卻能“經(jīng)冬猶綠林”。句中一個(gè)“猶”字,飽含著詩(shī)人的贊美之情。那么,丹橘經(jīng)冬猶綠,到底是因?yàn)楠?dú)特的地理優(yōu)勢(shì),還是本性使然呢?若是地理優(yōu)勢(shì)造成,也就不值得贊嘆了。因此詩(shī)人先用反問(wèn)句“豈伊地氣暖”一“縱”,又用肯定句“自有歲寒心”一“收”,令詩(shī)情跌宕起伏,獨(dú)具韻味。在古代詩(shī)文中,“歲寒心”多指松柏。詩(shī)人在此贊頌丹橘與松柏一樣具有忍受?chē)?yán)寒的節(jié)操,是別有一番深意的。
《橘柚垂華實(shí)》是漢代《古詩(shī)》中的一篇,其中一句“委身玉盤(pán)中,歷年冀見(jiàn)食”,以橘柚的遭遇抒發(fā)了詩(shī)人不被世用的憤慨。而本詩(shī)中的“可以薦嘉客”,就是“冀見(jiàn)食”之意。丹橘經(jīng)冬而不凋,不因嚴(yán)寒而改變節(jié)操,已經(jīng)很值得贊美;它結(jié)出豐碩的果實(shí),只想貢獻(xiàn)給他人,更可見(jiàn)它的品德高尚。按理說(shuō),如此優(yōu)良的樹(shù)木、果實(shí)是應(yīng)當(dāng)向嘉賓推薦的,無(wú)奈卻被重山深水無(wú)情地阻隔了!一句“奈何阻重深”,使人仿佛聽(tīng)到了詩(shī)人無(wú)奈的嘆息聲。
而“運(yùn)命惟所遇,循環(huán)不可尋”兩句,明確吐露了詩(shī)人托物言志之意:無(wú)論是丹橘還是人,其遭遇好壞與命運(yùn)相關(guān)。而命運(yùn)好壞的緣由則像循環(huán)往復(fù)的自然之理那樣,無(wú)法探究。這兩句詩(shī)委婉幽深,飽含著詩(shī)人復(fù)雜的感情。
在末尾,詩(shī)人用反問(wèn)語(yǔ)氣結(jié)束全詩(shī):世人只說(shuō)栽種桃李,莫非橘樹(shù)就無(wú)法遮陰、沒(méi)有功用嗎?在詩(shī)的前半部分,詩(shī)人已寫(xiě)明橘樹(shù)綠蔭耐寒、果實(shí)甘美,但它的命運(yùn)卻又如此多舛,這究竟是為什么呢?在《韓非子·外儲(chǔ)說(shuō)左下》中有這樣一個(gè)寓言:陽(yáng)虎對(duì)趙簡(jiǎn)主說(shuō),他曾經(jīng)親自培養(yǎng)了一批人才,然而當(dāng)他有危難的時(shí)候,這批人才卻都不幫他。因此陽(yáng)虎慨嘆道:“虎不善樹(shù)人。”趙簡(jiǎn)主說(shuō):“樹(shù)橘柚者,食之則甘,嗅之則香;樹(shù)枳棘者,成而刺人。故君子慎所樹(shù)。”只栽種桃李而不栽種橘柚,此類(lèi)“君子”,總不能算作“慎所樹(shù)”吧!
本詩(shī)不事雕琢卻渾然天成,兩個(gè)反問(wèn)句,更使詩(shī)情跌宕起伏。但詩(shī)的語(yǔ)氣始終是溫和敦厚的。無(wú)論是憤慨,還是憂傷,都是羚羊掛角,不著形跡,使全詩(shī)意境超然。